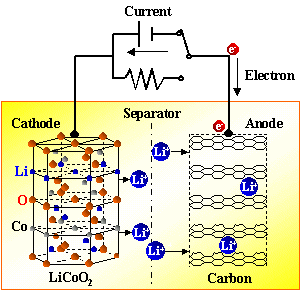ж–ҮеҢ–иө·еҲқдҪңдёәдёҺж”ҝжІ»гҖҒз»ҸжөҺзӯү并еҲ—зҡ„иҢғз•ҙеҚҺеӨҸеҠЁеҠӣпјҢеҸ‘еұ•еҲ°дёҺж–ҮжҳҺзӯүеҗҢпјҢзӣҙиҮіжҲҗдёәдәәзұ»зӨҫдјҡжҙ»еҠЁзҡ„з»ҹз§°пјҢе…¶еҶ…ж¶өе’ҢеӨ–延жҳҜдёҚж–ӯжү©еӨ§зҡ„гҖӮжҲ‘们常иҜҙзҡ„иүҜжёҡгҖҒйҷ¶еҜәгҖҒзҹіеіҒзӯүиҖғеҸӨеӯҰж–ҮеҢ–пјҢе°ұжҳҜиҝҷж ·зҡ„жҰӮеҝөгҖӮ既然жҳҜдәәзұ»зӨҫдјҡжҙ»еҠЁзҡ„з»ҹз§°пјҢе…¶еҝ…然жҳҜд»ҘзЁіе®ҡзҡ„йЈҹзү©жқҘжәҗпјҲеҶңиҖ•жҲ–з•ңзү§пјүгҖҒеҪўжҲҗиҒҡиҗҪдёәдёӨдёӘеҹәжң¬зҡ„еүҚжҸҗжқЎд»¶зҡ„гҖӮ
дёӯеҚҺж–ҮеҢ–иө·жәҗдәҺж–°зҹіеҷЁж—¶д»ЈеҚҺеӨҸеҠЁеҠӣпјҢиҮід»ҠдёӯеӣҪеҗ„ең°зҡ„еҫҲеӨҡж–ҮеҢ–е·®ејӮд»Қ然еҸҜд»ҘиҝҪжәҜеҲ°йҒҘиҝңзҡ„иҝҮеҺ»гҖӮиӢҸз§үзҗҰе…Ҳз”ҹж №жҚ®ж–°зҹіеҷЁж–ҮеҢ–йҒ—еқҖзҡ„еҲҶеёғжғ…еҶө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дёҖеҘ—вҖңеҢәзі»зұ»еһӢвҖқзҡ„жҰӮеҝөпјҢе°ҶдёӯеӣҪең°еҢәзҡ„иҖғеҸӨж–ҮеҢ–еҲ’еҲҶдёәе…ӯеӨ§еҢәзі»пјҡ
еҪ“然пјҢдёӯеҚҺеӨ§ең°зҡ„з–ҶеҹҹиҝңдёҚжӯўе…ӯдёӘж–ҮеҢ–еңҲзҡ„иҢғеӣҙпјҢиҖҢдё”и’ҷгҖҒи—ҸгҖҒз–ҶгҖҒиҘҝеҚ—еұұең°е’ҢжІҝжө·еІӣеҹҹд№ҹеҗ„жңүиҮӘе·ұзҡ„ж–ҮеҢ–зү№иүІеҚҺеӨҸеҠЁеҠӣгҖӮе…ӯеӨ§ж–ҮеҢ–еңҲпјҢжҳҜз”ұеҗ„ең°еҢәеҶ…йғЁдёҚеҗҢж–ҮеҢ–иһҚеҗҲиҒҡеҗҲиҖҢжҲҗзҡ„пјҢеҶ…йғЁеҗ„ж–ҮеҢ–д№Ӣй—ҙзҡ„иө·дјҸе’Ңз«һдәүд»ҺжңӘеҒңжӯўгҖӮиҖҢдё”е…ӯеӨ§ж–ҮеҢ–еңҲд№Ӣй—ҙпјҢеңЁж–°зҹіеҷЁж—¶д»Јд№ҹжҳҜеҪјжӯӨеҪұе“Қзҡ„гҖӮ
й•ҝжңҹд»ҘжқҘпјҢд»°йҹ¶ж–ҮеҢ–зҡ„жҲҗжһңеҚ жҚ®дёӯеӣҪж–°зҹіеҷЁж–ҮеҢ–зҡ„дё»жөҒдҪҚзҪ®пјҢйҡҸзқҖиҖғеҸӨиө„ж–ҷзҡ„зҙҜз§ҜпјҢдёӯеҺҹдёӯеҝғи®әзҡ„ж—§иҜҙпјҢе·Іиў«е…ӯеӨ§ж–ҮеҢ–еңҲе№іиЎҢеҸ‘еұ•иҖҢеҸҲзӣёдә’еҪұе“Қзҡ„и§ӮеҝөжүҖеҸ–д»ЈгҖӮжҜ”еҰӮпјҢиүҜжёҡзҡ„зӨјеҷЁдёҺдёңеҚ—жІҝжө·зҡ„зҺүзҹіж–ҮеҢ–пјҢ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еҗ„иҖғеҸӨж–ҮеҢ–дёӯзӯүзә§дёҺжқғеҠӣзҡ„иұЎеҫҒгҖӮжҜ”еҰӮпјҢжңҖж—©зҡ„зЁ»дҪңйҒ—еӯҳеҸ‘зҺ°дәҺж№–еҚ—йҒ“еҺҝпјҢжұҹжұүе№іеҺҹзҡ„зЁ»зұіж–ҮеҢ–дёҚж–ӯеҗ‘еӣӣе‘Ёжү©еј гҖӮжҜ”еҰӮпјҢеҢ—ж–№еҗҺжңҹзҡ„д»°йҹ¶ж–ҮеҢ–пјҢйІҒеҚ—иӢҸеҢ—зҡ„йқ’иҺІеІ—вҖ”вҖ”еӨ§жұ¶еҸЈиҜёж–ҮеҢ–пјҢдёҺжұҹжұүй—ҙзҡ„еұҲ家еІӯж–ҮеҢ–йғҪжңүзқҖдёҚеҸҜеҲҶеүІзҡ„иҒ”зі»гҖӮеҲ°дәҶи·қд»ҠеӣӣеҚғе№ҙеүҚпјҢеҢ—ж–№зҡ„зәўеұұж–ҮеҢ–з»ҸиҝҮеј е®¶еҸЈиҚүеҺҹпјҢжҠҳеҗ‘еұұиҘҝзҡ„жұҫжІіжІіи°·пјҢдёҺжқҘиҮӘе…ідёӯзҡ„д»°йҹ¶ж–ҮеҢ–еңЁдёҙжұҫзӣҶең°жұҮеҗҲпјҢжүҖд»Ҙйҷ¶еҜәж–ҮеҢ–д№ҹжңүзқҖжұҹжұүж–ҮеҢ–дёҺдёңйғЁжІҝжө·ж–ҮеҢ–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
дёӯеҺҹж–ҮеҢ–еңҲзҡ„дёӯеҝғең°еёҰжҳҜе®қйёЎеҲ°йғ‘е·һдёҖзәҝпјҢе…¶иҘҝиҷҪдёҺиҘҝйҷІең°ж–№ж–ҮеҢ–е…ізі»еҜҶеҲҮпјҢеҚҙжҳҜдёӯдәҡгҖҒиҘҝдәҡж–ҮеҢ–дј ж’ӯзҡ„йҖҡйҒ“пјӣе…¶дёңеҲҷжҳҜеұұдёңж–ҮеҢ–зҡ„иҝҮжёЎең°еёҰгҖӮиҖҢе®қйёЎеҲ°йғ‘е·һдёҖзәҝеҸҲеҸҜеҲҶдёәдёӨдёӘзі»еҲ—пјҡиҘҝж”Ҝдёәе®қйёЎдёҺйҷ•еҺҝд№Ӣй—ҙпјҢдёңж”ҜдёәжҙӣйҳідёҺйғ‘е·һд№Ӣй—ҙгҖӮдёӯеҺҹж–ҮеҢ–еңҲд№ҹи·Ёи¶Ҡи·қд»ҠдёғеҚғе№ҙеҲ°дәҢеҚғе№ҙпјҢжңүзқҖдә”еҚғе№ҙзҡ„еҲҶеҗҲдёҺиҝӣйҖҖгҖӮд»Һд»°йҹ¶зҡ„ж—©жңҹдёҺжҷҡжңҹпјҢиҝҮжёЎеҲ°е®ўзңҒеә„дәҢжңҹпјҢ然еҗҺеҲ°е‘Ёж–ҮеҢ–пјҢжңүзқҖзӣёеҪ“жҳҺжҷ°зҡ„иҝһз»ӯжҖ§гҖӮе…¶иҘҝж”Ҝзҡ„еҚҠеқЎзұ»еһӢе’Ңеәҷеә•жІҹзұ»еһӢйғҪжҳҜе…ідёӯең°еҢәе№іиЎҢеҸ‘еұ•гҖҒзӣёдә’дәӨй”ҷзҡ„ең°ж–№ж–ҮеҢ–пјҢжңҖз»Ҳеәҷеә•жІҹзұ»еһӢеҚ жҚ®д»°йҹ¶ж–ҮеҢ–дё»жөҒпјҢеҗ‘дёңжү©еј зӣҙиҫҫйғ‘е·һгҖӮеәҷеә•жІҹзҡ„еҪ©йҷ¶еҸҠзҺ«йӯӮиҠұзә№пјҢжҳҜе…¶дё»иҰҒзү№иүІпјҢиӢҸз§үзҗҰи®ӨдёәиҝҷдёҺ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иҮӘз§°вҖңеҚҺж—ҸвҖқе…ізі»еҜҶеҲҮ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д»Ҙй»„еёқдёәдё»зҡ„дә”еёқдј иҜҙзі»з»ҹпјҢжҒ°дёҺеәҷеә•жІҹзұ»еһӢзҡ„дј ж’ӯзӣёеҜ№еә”гҖӮ
дёӯеҚҺе…ӯеӨ§ж–ҮеҢ–еңҲзҡ„дәӨдә’иҒҡеҗҲпјҢеҠ дёҠйқ’й“ңеҲ¶йҖ гҖҒиҪҰиҫҶдҪҝз”ЁгҖҒе°ҸйәҰз§ҚжӨҚгҖҒзүӣзҫҠе…»ж®–зӯүжҠҖжңҜз”ұиҘҝдәҡиҮӘиҘҝеҗ‘дёңдј е…ҘпјҢиөӢдәҲдёӯеҺҹж–ҮеҢ–е·ЁеӨ§зҡ„иғҪйҮҸпјҢдҪҝд№ӢжҲҗдёәеӨҸе•Ҷе‘ЁвҖңдёүд»ЈвҖқж–ҮжҳҺзҡ„дё»жөҒгҖӮдёүеҚғдҪҷе№ҙеүҚпјҢиҘҝе‘ЁејҖеӣҪпјҢдёӯеҺҹзҡ„еҚҺеӨҸдёҺдёңж–№зҡ„ж–ҮеҢ–пјҢиһҚеҗҲдёәй»„жІіжөҒеҹҹзҡ„дё»жөҒж–ҮеҢ–гҖӮе…¶еҗҺпјҢжҘҡж–ҮеҢ–йӣҶеҗҲжұҹжұүдёҺеҚ—ж–№ж–ҮеҢ–зҡ„еҠӣйҮҸпјҢжҲҗдёәй•ҝжұҹжөҒеҹҹзҡ„дё»жөҒж–ҮеҢ–гҖӮзЁҚеҗҺпјҢдёңеҚ—зҡ„еҗҙи¶Ҡж–ҮеҢ–пјҢдёҖеәҰеҗ‘иҝҷдёӨеӨ§дё»жөҒж–ҮеҢ–еҸ‘иө·жҢ‘жҲҳгҖӮе…¬и®Өзҡ„жҳҘз§Ӣе…ӯйңё:йҪҗжЎ“гҖҒз§Ұз©ҶгҖҒжҷӢж–ҮгҖҒжҘҡеә„гҖҒеӨ«е·®е’ҢеҸҘи·өпјҢй»„жІіжөҒеҹҹе’Ңй•ҝжұҹжөҒеҹҹеҗ„еҚ е…¶еҚҠпјҢе°ұжҳҜеҚ—еҢ—ж–ҮеҢ–зҡ„з”ҹеҠЁеҶҷз…§гҖӮдёӯеӣҪеҮ еӨ§ж–ҮеҢ–еңҲз»ҲдәҺеңЁз§Ұжұүж—¶жңҹиһҚеҗҲдёәз»ҹдёҖзҡ„дёӯеҚҺж–ҮеҢ–гҖӮдёӯеҚҺж–ҮеҢ–жҳҜдёӯеҚҺжң¬еңҹж–ҮеҢ–пјҢдҪҶеҘ№д»ҚжҳҜдё–з•Ңж–ҮеҢ–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иҮӘеҪўжҲҗд№Ӣж—Ҙж—ўж·ұеҸ—еӨ–жқҘж–ҮеҢ–зҡ„ж»Ӣе…»пјҢд№ҹеҜ№дё–з•Ңж–ҮжҳҺдә§з”ҹзқҖйҮҚиҰҒеҪұе“ҚгҖӮжҖ»ең°жқҘзңӢпјҢеҢ—ж–№ең°еҢәеҙҮе°ҡеҫӘ规и№Ҳзҹ©гҖҒе®ҲйЎәе®үе‘Ҫзҡ„еӯ”еӯҹ儒家пјҢеҚ—ж–№еҲҷеҙҮе°ҡжҖқиҫ©гҖҒзҒөжҖ§зҡ„иҖҒеә„йҒ“家пјҢ并жҠҠеӨ–жқҘдҪӣж•ҷиһҚеҗҲдёәжң¬еңҹдҝЎд»°гҖӮ
дёӯеҚҺж–ҮеҢ–зҡ„иө·жәҗиҝңиҝңж—©дәҺе‘ЁжңқпјҢдҪҶеӨҸе•Ҷе‘ЁеҚҙжҳҜжһҒе…¶йҮҚиҰҒеҪўжҲҗйҳ¶ж®өпјҢе°Өе…¶е‘ЁжңқжҳҜеҚҺеӨҸж–ҮжҳҺзҡ„еҚҮеҚҺйҳ¶ж®өгҖӮеӨҸд»Јзҡ„еҺҶеҸІиҝ„д»ҠдёәжӯўеҸӘжҳҜдј иҜҙпјҢдәҢйҮҢеӨҙеӨҸйғҪзҡ„иҜҙжі•иҖғеҸӨиө„ж–ҷжң¬иә«е№¶дёҚж”ҜжҢҒпјҢеӮ…ж–Ҝе№ҙи®Өдёәе‘Ёдәәи®ӨеҗҢеӨҸдәәгҖҒд»ҘвҖңеӨҸвҖқиҮӘеұ…гҖҒи§Ҷе•ҶдәәдёәдёңеӨ·гҖӮеӨҸеҗҺж°Ҹж”ҝжқғжҳҜе‘ЁдәәдёәиҗҘйҖ е‘ЁзҺӢжңқеҗҲжі•жҖ§иҖҢеӨёеӨ§зҡ„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жІЎжңүеҸҜиғҪгҖӮж®·е•Ҷж–ҮеҢ–зҡ„дёӨеӨ§зү№иүІпјҢе°ұжҳҜз”ІйӘЁж–Үе’ҢзҺӢжқғгҖӮдёӯеӣҪж–Үеӯ—зҡ„жәҗеӨҙпјҢйҷ•иҘҝдёҙжҪје§ңеҜЁгҖҒжІіеҚ—иҲһйҳіиҙҫж№–гҖҒеұұдёңеӨ§жұ¶еҸЈзӯүйҒ—еқҖеҮәеңҹзҡ„йҫҹз”ІгҖҒйҷ¶еҷЁдёҠйғҪжңүеҲ»еҲ’з¬ҰеҸ·пјҢдҪҶж®·еўҹеҚңиҫһж–Үеӯ—е·ІзҰ»ејҖеӣҫеғҸпјҢе·ІзӣёеҪ“жҲҗзҶҹгҖӮеңЁж®·е•ҶпјҢзҺӢжқғеҺӢеҖ’дәҶж•ҷжқғпјҢе•ҶзҺӢдҪңдёәвҖңдёӢзҺӢвҖқдёҺвҖңдёҠеёқвҖқ并称пјҢи¶ід»ҘеҸ‘жҢҘе…¶ж–ҮеҢ–ж ёеҝғ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
е‘Ёд»Ҙж–№еӣҪд»Је•ҶпјҢеҚұжңәж„ҸиҜҶиҙҜз©ҝдәҺгҖҠе°ҡд№ҰгҖӢзҡ„е‘ЁеҲқж–ҮзҢ®дёӯпјҢеҪўжҲҗвҖңеӨ©е‘ҪйқЎеёёпјҢжғҹеҫ·жҳҜдәІвҖқзҡ„еӨ©е‘Ҫи§ӮпјҢе…·жңүжҷ®дё–ж„Ҹд№үгҖӮиҖҢе°ҸеӣҪеҜЎж°‘пјҢеҸӘиғҪвҖңе°Ғе»әдәІжҲҡпјҢд»Ҙи—©еұҸе‘ЁвҖқпјҢеҜ»жұӮдёҚеҗҢж–ҮеҢ–ж—ҸзҫӨзҡ„еҗҲдҪңгҖӮдёүд»Јд»ҺжӯӨ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зҡ„зҫҺеҘҪж—¶е…үпјҢж—¶е…Ҙдёңе‘ЁвҖңзӨјеҙ©д№җеқҸвҖқпјҢеҗ„иҜёдҫҜеӣҪе·ІеҸ‘з”ҹзҝ»еӨ©иҰҶең°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еҗ„ең°ж–№ж–ҮеҢ–еҠ йҖҹиһҚеҗҲпјҢвҖңзҷҫ家дәүйёЈвҖқж„Ҹе‘ізқҖдёӯеӣҪж–ҮеҢ–зҡ„еӨ§дёҖз»ҹеҝ…е°Ҷз ҙиҢ§иҖҢеҮәгҖӮд№ҹжӯЈжҳҜеңЁиҝҷж ·ж—¶д»Ј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е‘ЁдәәвҖңеӨ©е‘ҪвҖқеӯ•иӮІеҮәд»Ҙеҫ·ж”ҝгҖҒзӨјжІ»дёәж ёеҝғзҡ„儒家жҖқжғіпјҢ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жҖқжғідҪ“зі»зҡ„ж ёеҝғгҖӮ儒家дҝқеӯҳж•ҙзҗҶзҡ„е‘Ёжңқж–ҮзҢ®пјҢеҰӮ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гҖҠе°ҡд№ҰгҖӢгҖҠжҳҘз§ӢгҖӢзӯүпјҢжҲҗдёәзҷҫ家дәүйёЈзҡ„еҹәзЎҖгҖӮиҖҢиҖҒеӯҗзҡ„гҖҠйҒ“еҫ·з»ҸгҖӢеҘ е®ҡдәҶдёӯеӣҪе“ІеӯҰеҹәзЎҖпјҢгҖҠеә„еӯҗгҖӢеҲҷиҝӣдёҖжӯҘиӮҜе®ҡдёӘдәәзҡ„д»·еҖјгҖӮ墨家е’Ң法家еҲҷжҳҜеҜ№е„’家зҡ„еҸҚжӯЈгҖӮиҖҢй»„иҖҒе’Ңйҳҙйҳіе®¶еӨ©з„¶дёҺйҒ“家жңүзқҖе…іиҒ”жҖ§гҖӮ
йҡҸзқҖз§ҰжұүеӨ§дёҖз»ҹгҖҒйҡӢе”җеӨ§дёҖз»ҹй»„йҮ‘ж—¶д»ЈеҲ°жқҘпјҢдёӯеҚҺж–ҮеҢ–еңЁдёҺиҚүеҺҹж–ҮеҢ–зҡ„иһҚеҗҲдёӯпјҢеңЁдёҺеӨ–жқҘж–ҮеҢ–зҡ„дәӨжөҒдёӯпјҢдёҚж–ӯеҗёж”¶еӨ–жқҘж–ҮеҢ–зҡ„зІҫеҚҺиҖҢ蓬еӢғеҗ‘еүҚеҸ‘еұ•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дёӯеҺҹж–ҮеҢ–еҚ—移пјҢдёңеҚ—жІҝжө·ж–ҮеҢ–йҖҗжёҗжҲҗдёәдёңиҘҝдәӨжөҒзҡ„зәҪеёҰпјҢдёӯеҚҺж–ҮеҢ–з»Ҳ究зҷҫе·қе…Ҙжө·пјҢжҲҗдёәдё–з•Ңж–ҮжҳҺеҸІдёҠе”ҜдёҖжңӘжңүж–ӯеұӮзҡ„еҘҮи§ӮгҖӮд»ҺиҖҢиөӢдәҲйҫҷзҡ„дј дәәиҮӘдҝЎиҖҢеҢ…е®№зҡ„ејәеӨ§ж–ҮеҢ–е“Ғж јгҖӮ
жңүдёҖзӮ№еҝ…йЎ»жүҝи®ӨпјҢе‘Ёжңқж—¶жңҹпјҢдёӯеҚҺж–ҮеҢ–дёӯеҗ„з§ҚжҖқжғіж„ҸиҜҶзҡ„дё»дҪ“жЎҶжһ¶е·Із»ҸзЎ®з«ӢгҖӮ